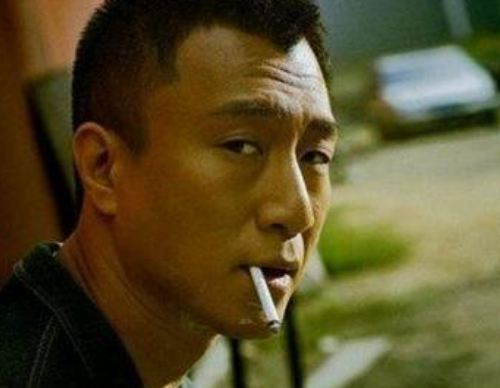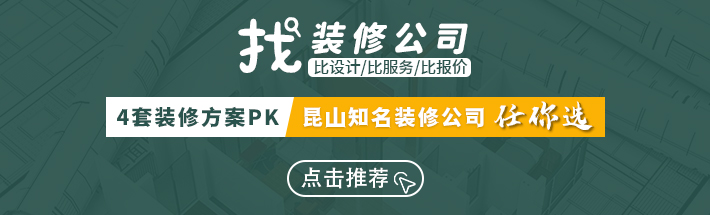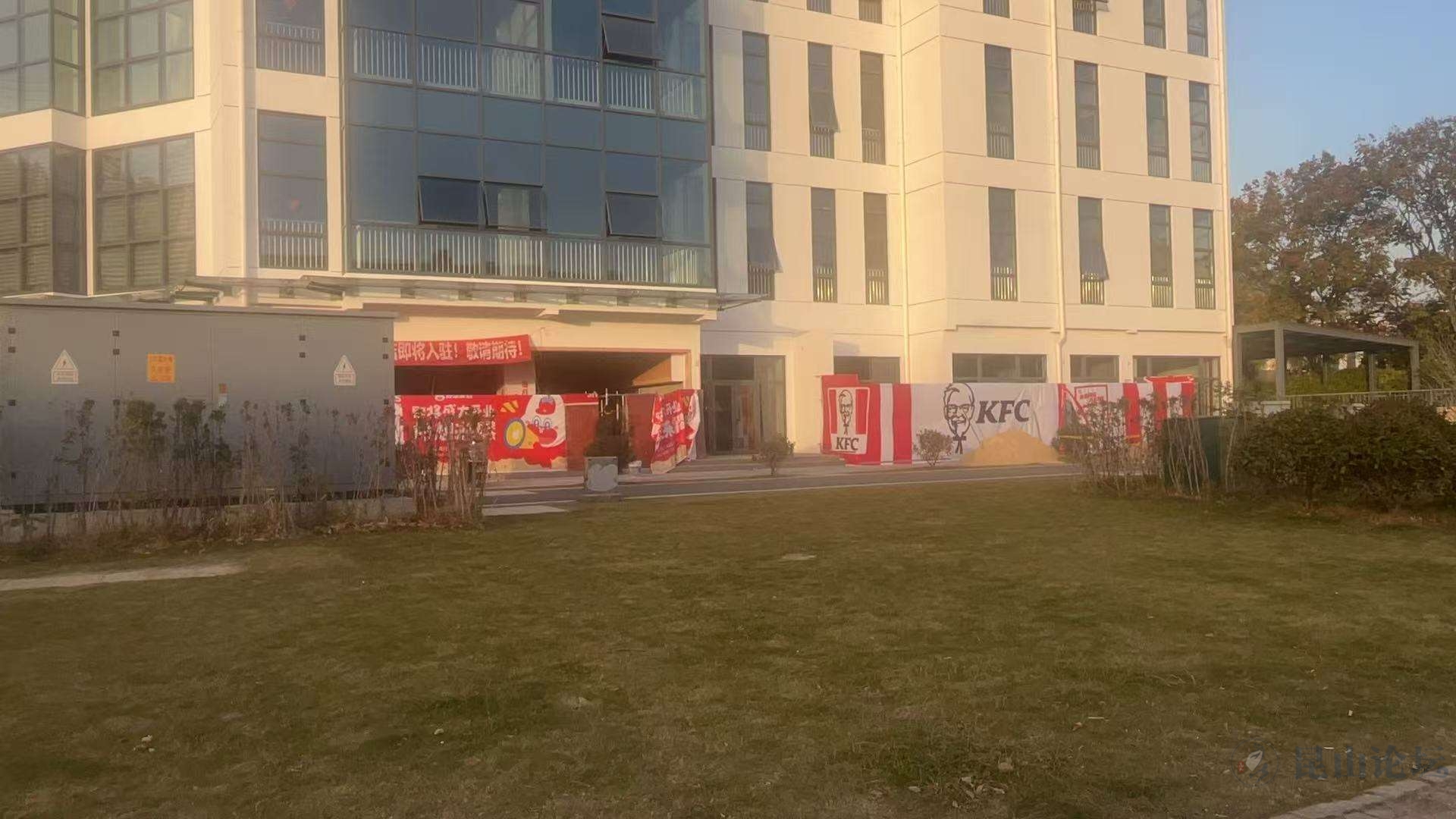今年的物理獎、醫學獎、化學獎全部頒給了人工智能...
黑體紫外非收斂,
以太漂移難證真。
大廈恢宏多贊譽,
烏云兩朵破金身。
忽聽地動驚雷響,
兩道霞光破寂穹。
變換空時相對論,
微觀量子躍虛空。
今年的物理獎看不懂,恭喜Hinton,懷念百年前的物理學盛世……
寫在新的一年
寫在新的一年 2024成為歷史,新的一年已經開始。時間是什么?如果世界的運行軌跡是設定好的,那么未來和過往沒有區別,當下只是一部大電影的當前播放畫面而已,若如此,則過往不值得留戀,未來亦不可期。如果世界充滿不確定性,那么過往的一切都已塵封,且一去不返,那些逝去的片段留存于我們的記憶中,曾經的擁有已然消亡,著實令人惆悵。而未來的變數既讓人迷茫也讓人期待。為了心中的期待,你需要做些什么......時間到底是什么?它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嗎?那為什么我的時間是越來越快的?它是我們主觀的一種體驗嗎?那為什么總是感覺時間不夠用呢?我們的童年我的父親非常關注人情世故之外的事物,我深受影響。這讓我長大后很久依然不太懂人情世故,我有時候為此自鳴得意,以為自己“超凡脫俗”;有時候卻會感到一點點自卑,以為自己在別人眼里不夠成熟。但現在看來,這似乎幫我減少了童年的某些“負擔”,孩子過早接觸人情世故不是一件好事,那容易讓他錯過身邊最美好的事物,比如想象那時候從沒吃過的南方水果如芒果是何等美味,想象遠處的山里一定有美好的故事,想象從來沒有去過的江南水鄉是如何美好……這些一旦和人情世故混在一起就煙消云散了。成長過程存在一個矛盾,不去努力磨平棱角就沒辦法獲得“成功”,但是太遷就他人就會失去自我。我們要尋找一個答案:什么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?對聲望的渴望背后是期望別人的肯定和尊重,對權力的追求背后是現實的不公,對金錢的追逐背后是缺失的安全感。當第一個變成虛榮,第二個變成凌駕于別人的虛妄,第三個變成貪婪的時候。此時追求的“成功”,只是一種“幸存者偏差”式的海市蜃樓,絕大多數人注定淪為這條道路上的炮灰。人到中年,感覺時間是加速的。童年的經歷奠定了每個人一生的基調,人生每時每刻都在和童年對話。未來的世界有些非常厲害的人物,大致可以預測未來的走勢,哪怕它不是朝著期待的方向發展。AI在大語言模型出現之前,AI的應用似乎主要在視覺和語音的識別,以及自動化、金融、游戲等過程中。自從大語言模型出現之后,專業人士對AGI(通用人工智能)的到來時間普遍非常樂觀,機器人產業也因此而開始進入即將爆發的態勢。如此深刻的變革對未來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,必定和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。這里有不可控的因素,也有我們個人可以提前做出應對的因素。不可控的因素,比如AI是否可控。針對這個因素我們普通人無能為力,只好聽天由命了。至于其它影響,比如個人和家庭關于教育的規劃似乎可以大致獲取一些端倪。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討論的話題,應該專門展開討論。有一點非常肯定:我們現在的教育內容、方式、理念等肯定需要做出極大的調整。現在做的很多事情必定是些無用功。生產方式現在的生產模式依賴規模化和分工帶來的成本效應,因此過分推崇消費,繁華甚至喧囂是社會生機勃勃的標志,每個個體被綁在這個機器上。副作用是周期的生產和消費的矛盾爆發,環境的代價,貿易摩擦..... 而一個繁華的森林卻沒有喧囂的感覺,有沒有可能未來的某一天,生產規模會變小,產業鏈條會收縮,在火星上也能不依賴很大的規模而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呢?那樣,小國也不再是大國的附庸,不再有生產力的失控....老子的理想是:鄰國相望,雞狗相聞,民甘其實,樂其業,老死不相往來。這種小國寡民的理想未來真有可能實現,基礎就是縮小產業鏈長度,就像一棵樹那樣,進去的是水和二氧化碳,輸出的是碳水化合物和氧氣。難道人的基本需求不也就是如此嗎?過多的物質需求其實是一個奴役自我的執念。降低消費是當下大環境的口號,也不只是一種被動。個人能駕馭欲望是一種修行,他們管這個叫自律。不是消滅欲望,而是不要讓自己成為欲望的奴隸。如果人類失去欲望,就會像卡恩博士設計的“老鼠之城”實驗的結果那樣,群體走向滅亡。而生命的意義就是“創造有序,并使之持續...” 所以那樣的結果是我們不愿看到的。這里修行不等于避世,應該像王陽明那樣在“知行合一”中修行。中華文化有很多不完美甚至很不好的地方,但是它能一直延續,除了東亞這塊兒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和兩千年的帝國統治外,也許還有它自己不一般的地方。只是在當今這個不再“封閉“的大環境下,它應當更加開放才行。除了開放還要包容。當然不是白左那樣的”政治正確“,社會需要回歸”更加科學的“理性。容許不一樣的聲音,只要它符合”更加科學的“理性,容許有些人避世。陶淵明選擇隱居,換來了針對當時社會的另一種視角和藝術上的成果-田園詩歌,他為一個群體注入了一種精神的內涵。以前,“造化”往往為學文科的人所設計,因為很多事情需要先和人打交道,而人的主題是非理性的。這些年技術大爆發,特別是AI落地后,很多事情繞開了人類,這種模糊的可操作的空間沒有了,管理世界的方式或許會更多基于所謂”第一性原理“,馬斯克參與社會治理應該是這一趨勢的一個體現。埃隆·馬斯克使用工程師思維改變世界 上面文章是幾年前我寫的,今天老馬居然真的從政了。只是那一年,AI還沒迎來大語言模型的爆發,機器人領域還是波士頓動力一家領銜。每個個人似乎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,是如此卑微,略顯無奈,甚至無助。仿佛只是歷史車輪上的一粒塵埃。然而每個生物體,特別是擁有智慧的人類,都是獨一無二的。一個人的神經細胞數量就有宇宙中的恒星那么多,當某個人的精神從某種束縛中釋放出來的時候,他將變得有意義,而不再卑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