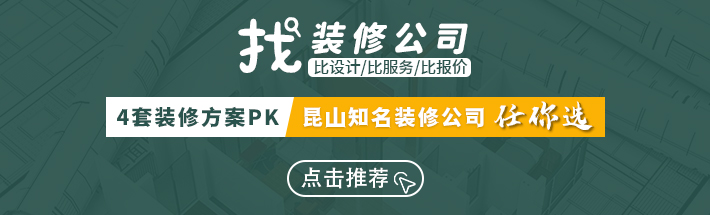【普法·微釋法】員工參加團建猝死,是工傷還是“自甘風險”?
工作之余
一些公司會組織團建活動以增進團隊情誼
若員工在單位組織的
集體活動中發生意外
能算工傷嗎?公司要擔責嗎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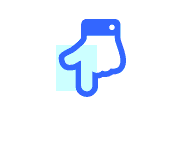
2021年3月,李成光(化名)入職某置業公司。入職一個多月后,合作方某建設公司為促進雙方合作、強化團隊凝聚力,舉辦銷售活動,并設置了拔河比賽活動環節。置業公司作為參與方,表示“這屬于公司組織的集體活動”,便在公司內部工作群通知員工參加,李成光與劉明(化名)被指派參加拔河比賽。不料,當天下午拔河比賽結束后,李成光突然臉色煞白,感到一陣劇烈不適,被緊急送往醫院。雖經醫院全力搶救,李成光還是在送醫當天因右室心肌病引發心跳驟停離世。

2022年1月,李成光的母親曾蕓(化名)向人社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。2022年7月,人社局經過細致調查,認定李成光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,從醫療機構初次診斷到他死亡,時間未超過48小時,符合《工傷保險條例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(一)項視同工傷的情形,因此認定為視同工傷(亡),并出具了《認定工傷決定書》。然而,置業公司卻不認可這份《認定工傷決定書》,隨即提起了行政訴訟,請求撤銷人社局作出的工傷決定。
案件的爭議焦點在于:
員工應用人單位指派
參加拔河比賽時發生傷亡
屬于自甘風險還是履行職務行為?
能否被認定為工傷(亡)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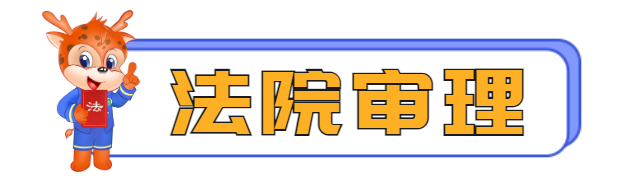
法院經審理查明,案涉拔河比賽由合作方建設公司牽頭舉辦,其目的是增進合作關系、強化團隊凝聚力,具有明確的業務關聯屬性。置業公司作為參與方,不僅將該活動定性為“公司組織的集體活動”,還通過內部工作群通知并指派李成光、劉明等員工參賽,上述行為表明置業公司對該活動的認可與主導,且活動與企業的團隊建設、業務合作推進存在直接關聯,屬于用人單位經營管理意志的直接體現。
從時間與場所維度上看,事發當日下午,李成光在固定工作時間內,先跟隨上級在售樓部開展本職工作,后服從上級指令參與在售樓部現場舉辦的拔河比賽,活動地點屬于工作場所的合理輻射范圍,時間未脫離工作時段,符合“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”的客觀要件。

本案中,李成光在參與公司指派的活動過程中突發疾病,經醫院搶救無效于當日死亡,從發病至死亡未超過48小時,符合《工傷保險條例》第十五條第一款第(一)項“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,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”規定的情形,應視同工傷。
自甘風險的構成需滿足“行為系個人自愿、與職務無關、用人單位未參與或指令”等要素,而李成光在上班期間服從上級的安排參與單位認可的集體活動,屬于服從勞動關系中“指揮與服從”原則的職務行為延伸,并非勞動者個人自發參與的、與工作無關的文體消遣,故不構成自甘風險。置業公司主張李成光的死亡屬于自甘風險、不應認定為工傷,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,法院不予采納。
綜上,法院依法駁回置業公司的訴訟請求。公司不服一審判決,提起上訴。廣西貴港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,裁定駁回上訴,維持原判。

單位組織的團建活動屬于工作職能延伸,這一認定既有明確的邏輯支撐,也符合現實中的權利義務關系。
“因工受傷”與“自甘風險”的界限,核心在于行為與工作的關聯性,背后是法律對“責任歸屬”的界定,也蘊含著對勞資雙方權益的平衡考量。《工傷保險條例》規定“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,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”應當認定為工傷,其中“工作原因”既包括直接執行職務的行為,也包括服從單位安排、為完成工作所必需的關聯行為。
勞動關系中,員工的職務行為是單位意志的延伸,單位通過員工的具體行為持續獲益,自然應對該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承擔起兜底責任。反之,若員工行為完全出于個人意志、脫離工作范疇,單位既未從中獲益,也無法進行合理管控,要求其承擔責任則有違權利義務對等原則。這一區分既堅守了對勞動者的保護底線,又明確了個人行為的責任邊界,防止過度加重單位負擔,在保護與公平之間實現平衡。
來源:尚法昆山